2025年4月16日下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举办“北外文华讲堂”系列讲座,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中国俗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戏曲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明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杜桂萍教授作题为《才子、仙官与诗圣:杜甫形象的戏曲建构》的学术报告。讲座由中文学院名誉院长詹福瑞教授主持,学院党总支书记蔡芝芳、副院长白亮、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教师及学生六十余人参加此次讲座。

杜教授先对元明清戏曲作品中的杜甫书写情况进行了概述。唐代诗人杜甫以其卓越的诗歌成就和人格魅力影响后世,以杜甫及其作品为创作题材者元代有3部,明代有6部,清代则达到了9部。不仅杜甫生平行迹成为戏曲题材的青睐对象,其诗歌意象、作品片段等亦深刻地濡染戏曲文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接受现象。这些都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杜甫之影响在戏曲创作领域的上升态势,与本时期诗歌领域的宗唐尊杜发展过程相一致。

接着杜教授结合具体戏曲作品进行讲解。在杜甫的一生之中,其曲江游春、金门献赋、浣花溪生活的片段最为戏曲家所属意,“长安十年”与“川中五年”也是杜甫戏曲书写的重点。这些场景为戏曲家想象杜甫提供了最为合适的空间,戏曲家也经由创作表达出自身的情感心理。
杜甫的“才子”形象,是明清戏曲家们努力着墨之处。杜诗成为构成戏曲文本、塑造形象不可或缺的元素,或是直接采用杜诗,或借助杜诗改写、重写,杜甫形象往往以自己的诗歌作品登场。但明清也各有侧重:在明代戏曲家,“风流才子”“诗酒风流”的形象与元素,经由王九思《曲江春》的创作,真正定格在了沈采《四节记》的书写;在清代戏曲家,忠君爱国、关心民瘼的儒家情怀是杜甫戏曲创作的突出特征,“才”依然是叙事、抒情的主体,不过已经从单纯的诗才扩容为经天纬地的治国之才,正如《诗中圣》《一斛珠》等作品所体现的那样,“致君尧舜”与“许身稷契”才是杜甫的人生理想、身份标识。
杜甫的“仙官”形象,是为了“补恨”与“写心”。出于为杜甫补恨的目的,戏曲家通过改写与虚构等手段,摹写其中进士、为官等生命故事。代言体创作赋予戏曲家巨大的“权力”,尽意挥酒创作激情,建构心目中的杜甫并借以自喻。这种创作形式也是戏曲文体之于诗文的优长所在,自喻性以及与之相关的吐臆抒感更为戏曲作家所心仪,这是他们塑造杜甫形象的重要方式,也是他们选择以戏曲表达对杜甫敬意的原因。
杜甫的“诗圣”形象,在戏曲领域也经由各朝塑造而得以完成和巩固。元明清时期的诗歌宗唐与戏曲尊杜关系密切,戏曲作家借助文本参与了杜诗经典化的进程。与真实再现唐代历史上的杜甫相比,戏曲家更希望在非常自我的视野中进行阐释和抒情。戏曲家多有意突出彼此的休戚与共、相互欣赏,李杜之比由“高下”进入“合璧”,杜甫形象借助李白更加彰显其诗圣地位。
杜教授在最后总结道,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不朽作家,“才子”之杜甫、“仙官”之杜甫、“诗圣”之杜甫,其书写始终与“情”相关。明人侧重于诗酒风流、真诚人性,而清人着力于社稷民生、儒家情怀,但杜甫历经元明清三代日益成为“诗圣”的过程,实际上借助戏曲的“体贴人情”而达成了另一面向的阐释。戏曲家们从个人的际遇出发对杜甫及其作品进行个性化阐释,杜甫因此作为历代文人的知音和情感载体,获得了另一种形式的接受。随着读杜、注杜、评杜等渐为时尚,杜甫及其诗歌作品进入戏曲文本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新的批评话语方式。
在提问交流环节,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教师徐晓峰、青子文和周健强分别就清代杜甫题材戏剧数量的变化、杜甫戏曲在当时的受众情况与受欢迎程度、戏曲本身是文人自娱还是观众导向创作、戏曲中其他唐代诗人形象的案例、相比李白是否杜甫题材戏曲更受欢迎等问题,与杜桂萍教授进行了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教师张霖认为杜教授以未被经典化的戏曲作品考察杜甫经典化问题,独具文心,对面临经典化困境的现当代文学批评的研究来说,具有方法论的启发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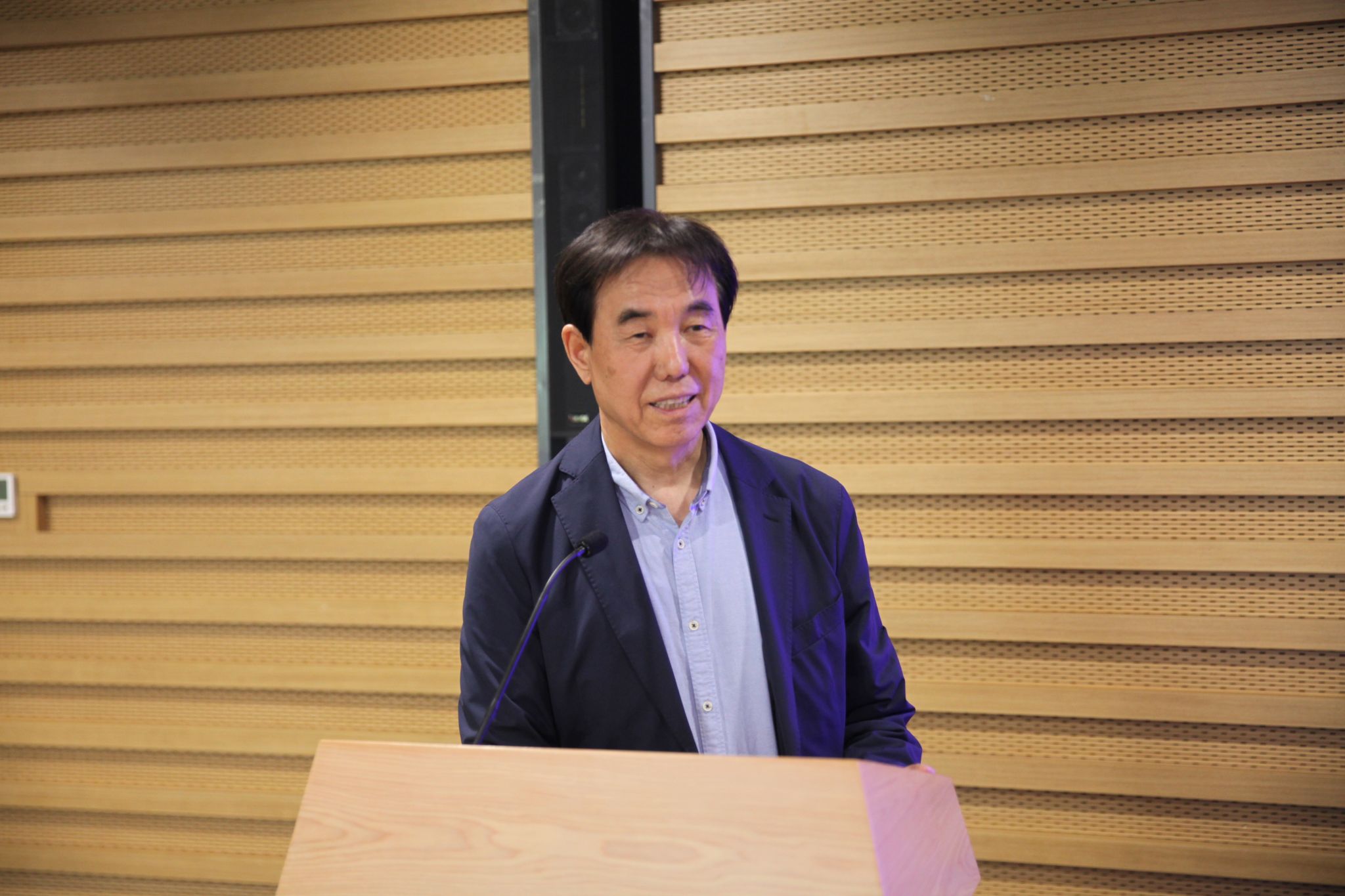
詹福瑞教授的总结致辞指出,希望教师之间的学术交流能带动学生成长,积极参与学术话题。杜教授的杜甫“入戏”研究,为之后的文学研究拓宽了新的思路。鲜少有人关注到戏曲中的诗人经典化路径,而事实上研究本就是发散性研究,是开放而非拘谨的,打通各学科之间的壁垒,也是为研究提供重要的方法和路径。

撰稿:戢默涵
审校:徐晓峰
审核:蔡芝芳